应浙江师大附属小学项雪寒校长之邀,11月26日下午,傅惠钧教授在附小作了一场题为“同义比较:文本推敲的一种有效方法”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附小宋梦萍老师主持,浙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王国均副教授、人文学院教务办主任蒋晓玲、附小全体语文教师以及师大语言学研究生等3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据项校长介绍,上次“基于‘推敲策略’的深度学与教”项目研讨后,学校为全体语文老师购买了傅老师的《修辞学与语文教学》一书,要求老师们系统研读,应用于教学与研究。项校长希望傅老师能够就大语言修辞对接语文教改的有关重点内容作一些阐释和交流,本次讲座,正是应此需求而专门作的安排。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宋梦萍老师对傅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参与活动的师生作了介绍。傅老师开场讲到,尽管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在语言学,但多年来对于基础教育的参与和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师大,由于师范专业教育改革和学院教学管理的需要,对语文教学的探讨有了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热情。他对王国均副教授多年来一直热心关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实践教改新理念的态度和做法大加赞赏,对附小语文老师教学改革的热情和行动力由衷钦佩。
傅老师的讲座从“什么是同义比较”“同义比较对文本推敲的价值”和“同义比较在文本推敲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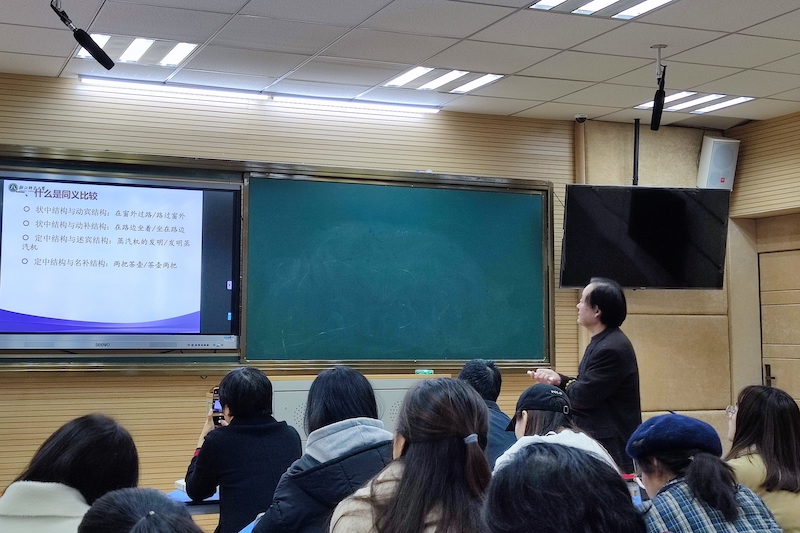
在阐释何谓“同义比较”时,傅老师先引入“同义形式”概念。他说,同义形式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表示相同或相近意义,但在表达效果上具有细微差别的语言形式。从语言系统说,有语言的同义形式和言语的同义形式之分;从语言单位说,有词语同义形式、结构同义形式和句式同义形式之别。
傅老师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同义形式,修辞表达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同义形式的选择或创造。他举例说,关于“死”可以有各种说法,诸如“去世、牺牲、逝世、作古、圆寂、归西、完蛋、闭眼、挺腿”等等,陶渊明在《自祭文》中说,“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饶毅在毕业致辞中说,“在你所含全部原子再按热力学第二定律回归自然前,它们既经历过物性的神奇,也产生过人格的可爱”,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称,“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划上句号”,其中“死”的表达也各不相同。傅老师说,这种不同的表达有的甚至是不可穷尽的,比如有人会用“去见马克思”表达“死”的意思,其实“去见XXX”这个格式,只要填进去一个死者的名字,均可表达“死”的意思。这些不同的表达在修辞意味、感情基调、语体色彩、语义侧重、适用对象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差异。他说,所谓同义比较,就是在文本解读中,引进相关的同义表达形式与原文进行对比,来分析作品语言的优劣得失,从而把握语言应用的规律。
傅老师以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上)中的课文《山中访友》为例,引进李汉荣的原文与课文的改笔作比较:
原文:走出门,就与含着露水和栀子花气息的好风撞个满怀。早晨,好清爽!
课文:走出门,就与微风撞了个满怀,风中含着露水和栀子花的气息。早晨,好清爽!
傅老师分析道,这里写作者出门时刹那间的感觉,原文的句法突出显示跟作者“撞个满怀”的不是一般的风,而是“含着露水和栀子花气息的好风”。正因此,才用上“撞个满怀”这样异乎寻常的比拟手法。课文变合叙为分述,基本语义未变,但由于把修饰语后移独立表述,相关信息也因此滞后呈现,从认知修辞来看,表达的先后往往反映认知的先后,因此原文表达的认知结果就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编者的改稿显然不如作者的原文。

在讲“同义比较对文本推敲的价值”时,傅老师主要谈了四点:1.同义比较能将阅读教学的关注点引向言语形式;2.同义比较能为寻常语言赏析提供有效抓手;3.同义比较能化静态为动态,有助于将语用规律内化为学生的语言能力;4.同义比较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分析课文语言时,傅老师举到人教三年级(上)贾平凹《风筝》中的例子:
原文:我们精心地做着,把春天的憧憬和希望都做进去。
课文:我们精心做着,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贾平凹原文,承上句的“做一个蝴蝶样儿的吧”,运用了拈连的修辞手法,将“做”顺势拈来,使表达显得更加巧妙,更加耐人寻味。课文的表述平实规范,但缺乏灵气。这种实例比较,充分体现了教学价值。对于寻常语言分析,傅老师举到四年级课本《触摸春天》一文中的语句:
原文:昨天早晨,我在草地上做徒手操,安静在花树丛中穿梭,因为常在其间流连,她走得很流畅,没有一点磕磕绊绊的感觉。
傅老师指出,课文编者将“昨天早晨”改作了“早晨”。“昨天早晨”是一个以作文时间为基准的时间定位,具有精确性。只说“早晨”则富有弹性,可以是昨天早晨,也可以是春暖花开时的任何一个早晨,具有模糊性。作者无非告诉读者,这是发生在春天一个早晨的一段经历,模糊比精确似乎更有张力。傅老师强调说,此处的表达,一般老师们很少会从修辞角度予以关注,但通过同原文相比较,就能认识到语言形式和表义上的差别。这就是同义比较能为寻常语言赏析提供有效抓手的明证。
关于“同义比较在文本中的应用”,傅老师主要从比较方法的角度作了阐释。他认为应该采取异文比较和变换比较相结合、内部比较与外部比较相结合等方式来提取材料、组织教学。“异文比较”是引进与课文表达“同中有异”的现成的语言现象来比较分析,上面所举各例都属于这种方法。傅老师说,从小学教学的角度讲,目前入选教材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编者润改的。这些改动,有的改得好,有的改得不好,可以广泛搜集,用于课堂比较。傅老师在讲座中分析了大量原文与课文比较的实例,从多个角度给老师们以启示。而“变换比较”是指将课文中特定的修辞形式临时改变为另一语言形式,再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其手段主要是增添、删减、移位、改换。傅老师说,这种分析方法在先秦两汉解析经书的《公羊传》和《穀梁传》等著述中已经发凡起例。通俗一点可以说成,“增添词语读读看”“删减词语读读看”“换个语序读读看”“变个句式读读看”“改个词语读读看”等等。比如朱自清《春》的开头,“盼望着,盼望着”,删去一个“盼望着”,比较一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近”改成“重”可以吗?为什么?“变换比较”随时可以灵活应用。而无论是“异文比较”还是“变换比较”,都存在内部比较和外部比较两个方面。
讲座进行到讨论环节,大家畅所欲言,提出问题,发表各自意见。王国均老师针对讲座中提到的《山中访友》的例子指出,傅老师从认知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应用,他本人很受启示,因为很少能有老师这样去思考问题、分析语言,希望傅老师下次有机会就这个方面单独作一场专题讲座。
项校长就小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雪白的雪”“雪白的白云”一类错误表达,向傅老师询问解决的办法。傅老师指出,从语言形式本身看,此类表达确实存在问题,应该告诉学生表达不妥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语言表达,我们会习惯性地、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进行评价。但在应用中,对和错往往并不绝对,学生作文中的此类现象,有时也不宜简单否定,当放到具体情境中去分析。只要适应题旨情境,表达就是合理的。更不要说,修辞中还有“飞白”艺术呢!
李红果老师提出,三年级有一篇课文《金色的草地》,对于新版教材将其末尾一句进行删除的原因,老师们不能理解。专门就此请教了傅老师。教材原文是:
有一天,我起得很早去钓鱼,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而是绿色的。中午回家的时候,我看见草地是金色的。傍晚的时候,草地又变绿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到草地上,仔细观察,发现蒲公英花瓣是合拢的。原来蒲公英的花,就像我们的手掌,可以张开、合上。花朵张开时,花瓣是金色的,草地也是金色的;花朵合拢时,金色的花瓣被包住了,草地也就变成绿色了。
多么可爱的草地,多么有趣的蒲公英,从那时起,蒲公英成了我们喜爱的一种花。它和我们一起睡觉,一起起床。
新版教材中把“它和我们一起睡觉,一起起床”句删去了。傅老师在与老师们的交流互动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表达可以有时间和空间两种不同的解读。“一起”可以是“同一个处所”之意,是空间上的“一起”;也可以是“一同”之意,是时间上的“一齐”。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它和我们”在时间上的“一齐”:花睡觉了,我们也睡觉,花起床了,我们也起床。他认为这些容易引起歧义的文字,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若改作“一齐”,可以消除歧义。傅老师进一步问,那为什么不把“一起”改作“一齐”,而要把整句删除呢?李红果老师认为,“从那时起,蒲公英成了我们喜爱的一种花”这句让人觉得已经是结句了,再加上一句,显得有些多余。傅老师充分肯定了李红果老师的见解,并进一步指出,即使要保留,也不能留在文章的最后,而应移到前一段结尾。

讲座接近尾声时,傅老师特别强调,“同义比较”将修辞与词汇、语法有效结合起来,体现了大语言修辞的旨意。在语言的运用中,任何词汇、语法形式都是修辞形式,是修辞意义的载体。因此,任何形式的变动都会影响到修辞旨意的表达。“同义比较”能有效培养学生敏锐的语感,长期坚持做,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定会多有助益。傅老师进一步指出,“大语言修辞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支撑,它可以有效推动语文教学回归到语言表达的本体上来。他希望有更多的语文老师能够借助大语言修辞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推动语文教改。
整个讲座持续近三个小时,项校长最后作了总结并致衷心感谢。
(文:张逸添、冯学琴 / 图:王红 / 编辑:王蕾、李艳芝 / 审核:殷晓杰)